电话:010-82851088
邮箱:bj@hjg.org.cn
邮编:10019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31号院新奥特科技大厦8层

(微信扫一扫二维码关注)
2023年9月1日即将迎来哈军工建校70周年,哈军工北京校友会于2021年12月21-23日在中灿苑慰问探望老校友,在校友会中灿苑联络员的协助下,组织了座谈会,共忆往昔峥嵘岁月。
第一次座谈会
2022年12月21日上午9时许,校友会常务理事李卉带领校友会会员翟宇豪、朱永康等前往中灿苑开展第一次座谈会,慰问探望老校友。地址选在杜淑兰家中,除60级校友杜淑兰(79岁)外,与会者有教员王年华(90岁)、52级校友李贤方(89岁)、58级校友谢多礼(87岁)、中灿苑校友会联络员、61级校友干韫胜(79岁)。

校友会李卉(左一)、校友李贤方(左二)、校友杜淑兰(左三)、校友谢多礼(左四)、教员王年华(右四)、校友干韫胜(右三)、校友会翟宇豪(右二)、校友会朱永康(右一)

教员王年华在座谈会上发言
作为教员的校友王年华在茶会上首先发言。
王老回忆到:“我贫农出身,自幼与母亲二人相依为命。1951年,我离开重大,投笔从戎,进入成都空军第四预科中队进行为期一年的思想教育。但由于我鼻窦弯曲,无法成为一名飞行员,就转入洛阳空军干部学校学习参谋专业。
1953年哈军工成立需要干部,因为我兼具大学生和党员身份,就被调入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担任年级主任,主要负责教务工作。直到1961防化兵学院建立,我才离开哈尔滨奔赴长春。
在反右期间,系里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就将我们班的七名学员划定为右派。但这七位同学认为我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所以一直对我怀恨在心。 而我因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学生,这是我工作中的一个遗憾。”
王老还为大家讲述了六十多年前在校长陈赓的带领下,与战友、校友一起建校的峥嵘岁月。王老特别提到自己和全体教职工是“端盘子的”,众多校友数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地奋斗在教务岗位上,大家有一句口口相传的话就是“工作在哈军工,死了就埋在鸡落寺”。

60级空军工程系/电子工程系校友 杜淑兰
校友杜淑兰从自己高中毕业开始回忆,为大家讲述了自己1960年从北京市女二中(现东直门中学)毕业之后,作为工农子弟被推荐参加哈军工的考试、体测、入校军事训练、学习到毕业工作的过程。
在结束了5年半的大学时光之后,杜淑兰先后进入总参三部、六部工作,负责侦听装备、指挥自动化装备的测试。老人特别提到当时的工作地点,是在作为前线的福建矾山,每当天朗气清之时就可以远远地看到台湾岛。
由于正值我军军事装备大发展阶段,一心扑在工作的杜淑兰竟连续七年没有回家过春节。 在校友会的年轻人问及此事时,老人家有感而发,为校友们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清苦生活,是党和国家将自己培养成一位大学生,自己只能用努力工作这一种方式来回报党和国家的恩情。

53级空军工程系校友 李贤方
校友李贤方为大家讲述了当年哈军工的建校过程,由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深感到了我国与美国在军事技术领域上的差距,所以毛主席将陈赓大将从朝鲜战场调离,回国组建哈军工。
据李老回忆,哈军工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李老在校时主修的专业是人数最少的空军工程系气象专业,在招生初期只有20个人,其中6人从军队调入,其余14人从地方考入。然而在毕业之时只有16人顺利完成了学业。 同时李老也夸赞了哈军工的师资力量,特别是师生比,在仅气象专业就高达3:20。
李老特别提到在校期间,校长陈赓为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说:“陈赓大将的作风特别好,一天到晚就是扎根在老师和学生中间,时不时和同学们聊天,一点领导的架子都没有。”
毕业之后,李老前往国防科委任职,后调入总参气象局。在工作中最令其影响深刻的是1972年由于气象原因多次推迟卫星发射。时任气象室主任的李贤方被叫入发射中心主任办公室面谈,中心主任对他说到:“现在你就是司令员,你说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钱老由此深刻意识到了军事气象的重要性,年纪不满三十的李贤方深感肩上压力之大。彼时恰逢钱学森也在发射现场,李老就也趁此机会向钱老反映了人手不足的问题,钱老立刻着手解决,不到几个月的时间,20多位哈军工气象专业的毕业生就站到了李老面前。
也许是气象专业过于小众,诸位老校友在听过分享之后纷纷向李老了解有关气象专业方面的知识。

59级炮兵工程系/防化兵工程系校友 谢多礼
校友谢多礼为我们分享了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到回国后进入哈军工学习的过程。
谢老回忆说: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军事装备品种、性能、数量都比较落后,能打败敌人全靠干部战士高度的智慧和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参加过战斗的人,都对培养武器装备建设人才的基地—‘哈军工’高度向往。
他说:他于58年进入哈军工。因为参军时只有高中一年级的文化水平,就先安排在预科队学习高中文化。59年预科毕业后,与地方考入的高中毕业生,一起分入军工炮兵工程系,防化兵工程专业学习。1962年转入防化兵工程学院学习。于1964年毕业。
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防化兵总部机关工作。主要负责防化装备的采购与质量管理,以及相应的人才培训工作。谢老对于自己的工作经历并没有太多的描述,重点强调了哈军工的学习生涯给自己带来的影响。谢老说:“无论是政治思想上的坚定、严肃认真作风的养成,还是技术知识能力的扎实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哈军工的经历对我之后的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职期间有效地为军队装备建设服务,这也是哈军工建校的宗旨,改进我们的武器装备。
我1989年接到退休的命令,退而没休,仍以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以及哈军工精神,继续参与有关的编史工作24年,直到2015年才彻底退休。时年已81岁。”
最后,谢老充分肯定了哈军工在建校近七十年的时间里为我军装备建设做出的贡献。
大家一致认为哈军工的建立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哈军工精神始终是激励大家前进的动力。
21日下午2时许,校友会一行人来到院士钱七虎校友的家中探望。

54级工程兵系校友 钱七虎(左二)
中国工程院院士、八一勋章获得者钱七虎时至今日依然奋斗在祖国科研一线。经干韫胜的联络下,校友会一行人有幸在钱院士百忙之中的午饭间隙探望了他。由于时间紧,钱老与校友会一行人未展开交谈。
下午3时许,校友会一行人前往因身体原因无法参与座谈会的57级校友叶谷音(87岁)的家中慰问探望。

57级炮兵工程系校友 叶谷音(中间)
见到校友会一行人,叶老眼含热泪,心情无比激动,深情的讲述了自己学习、工作和战斗的经历。
叶老同样是抗美援朝之后从军队中选调进入哈军工学习的。
叶老首先表达了对哈军工的感恩之情,之后和校友会一行人讲述了他在哈军工上学期间,学员们不仅需要刻苦完成学业,在课余时间还要进行农业生产、站岗等活动。 成绩优异的叶谷音在农业生产上同样是一把好手,特别是他所在班级种植的葵花籽,颗粒大而饱满,每次都被全校学生抢着要。叶谷音等人将剩余的葵花籽拿到市场上售卖,并将所得的两元钱上交学校。
毕业之后,叶谷音进入到总参四部工作,参与了多种型号雷达的研制工作,在电子战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建树。 精通业务的叶老和校友会一行人讲述了我国仿制法国响尾蛇防空系统雷达的过程,并简单讲解了雷达的多种定位方式。
叶老讲述时间最长的,是在抗美援越战场上,如何在规避美国“百舌鸟”反辐射导弹的同时,锁定击落U-2侦察机的过程,令校友会一行人拍案称奇。
第二次座谈会
12月22日上午9时许,校友会监事殷红兵带领校友会技术人员翟宇豪、朱永康前往中灿苑开展第二次座谈会,慰问探望老校友。地址选在陈学中的家中,除53级校友陈学中(91岁)外,与会者有56级校友马金福(86岁)、55级校友史余山(85岁)、61级校友于树藩(79岁)、中灿苑校友会联络员、61级校友干韫胜(79岁)。


校友马金福(左一)、校友史余山(左二)、校友陈学中(左三)、陈学中夫人(左四)、校友于树藩(右二)、联络员干韫胜(右一)

53级空军工程系校友 陈学中
校友陈学中在茶话会上首先发言。
陈老对我们说:“1951年我在河南大学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求我去参加一个考试。1953年1月份,组织上通知我去哈军工上学。回顾我这一生,这可能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因为当时大家都在说哈军工毕业之后就可以成为一名军事工程师。第二就是听说哈尔滨被誉为东方莫斯科,所以能去哈军工上学我高兴得很。”
“当时我们第一期学生只有两三百号人,学校还没有什么校舍,大家上课有活动什么的都是在一个文庙里进行。 开学第一天陈赓院长为我们大家开会,当时有学生得知陈院长年轻的时候背过蒋介石,就在会上问了这个事情。 陈院长当时非常幽默的回答说:‘你以为我愿意背他呀,那时候国共合作,那是党交给我的任务。’ 还有学生问陈院长:‘解放战争的时候你带兵往广东打,为什么不顺带把香港解放了?’ 陈院长回答说:‘你以为我不想解放呀,当时香港的问题属于国际问题,我得请示中央,中央说先放一放,就到现在了。’”
毕业后陈老留校担任教员,后被分配到21基地,参与了我国的核试验工作。接到调令的那天,陈老仍记忆犹新:“我想这是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培养我这么多年是我报效祖国的时候了。由于时间紧急,要求我们三天之内就带着家属一起出发。 到达了新疆之后,我被分入气象组室。 当时任务非常紧,进行实验的气象条件已经确定,我们几个人马不停蹄的就赶往乌鲁木齐气象台开始搜集气象资料,和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进行比对。 我们第一次的核试验定在十月份,由于出色完成了任务,组织上给我们气象单位一个集体一等功。之后的两次核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我们一共立了四次集体一等功。”
文革开始后,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基地开始批判聂荣臻和张爱萍,陈老由于在第一次核试验前夕专心于工作,被人污蔑为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被迫于1969年离开军队,复员回到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八车间做了一名包装工。
陈老说:“刚刚离开基地回到地方的我空有一身本领而无处发挥,每天都处在一个闷闷不乐的状态中,但随着和工人相处时间的增加,我渐渐感觉到和大家每天一起又说又笑的生活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不久,后来我被工人推选为组长,除生产之外还要负责工人们的日常学习,天天为工人同志读报、读毛主席诗词。 后来工厂的党委书记想要把我调入厂政工组,由于当时政工组工作的特殊性,我就没有接受。”
不久,陈老被调入开封师范学院“以工代干”担任教师,主讲概率论。 陈老回忆到:当时上课第一天,我看到教室的卫生状况十分糟糕。想想当年我们在哈军工的时候,每天打扫教室都要拿着抹布跪在地上擦,因此我当时就决定这节课不上了,全体打扫卫生。时后我的两个助教和我讲:陈老师这样子做,工农兵是要开你的批斗会的,会说你是“封资修”。我说:‘难道工农兵就要在垃圾堆里上课吗?’ 之后每逢遇到我的课,同学们都会提前将教室打扫干净。”
1977年张爱萍调任国防科委主任之后,陈老写信给张将军反映自己的情况。不久之后接到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寰的来信,承认了当年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下,基地处理不当将其调离军队的问题,不久之后陈学中回到了21基地,并在后来参与了我国新型导弹研制的相关工作,为导弹的弹体材料的使用提出了宝贵意见,后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最后陈老总结到:“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哈军工的学习是非常扎实的,尤其是每个专业的老师都是其领域的尖端人才,我们后来在工作中取得的突破都得益于当年打下的基础。”

55级空军工程系校友 史余山
校友史余山为我们主要讲述了他工作的经历。
中学毕业之后,史余山来到北京作为留守预备生学习俄语,由于中苏关系破裂,留苏预备生被取消,史余山转入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气象专业学习。
1961年哈军工毕业之后,史老被分入海军司令部,1962年到青岛的流亭机场负责气象工作。
64年由于工作需要,史老被调入总参气象局。史老回忆说:“当时把我调入北京也不和我说要干啥,搞得还挺神秘,说先让我休息两个月。结果休息了没多长时间,和我说让我到新疆去搞核试验,负责核试验的气象保障。当时和我交代的非常多,第一个就是要保密,对自己的家属都不能说去干啥,只能说我有事儿。 我当时一听说去新疆还觉得不错,从来没去这么远的地方,还感觉挺新鲜。”
“在第一次核试验结束之后,我在65年回到北京参加总参气象室成立的准备工作,当时老马(马金福)已经在了。 在气象室也是负责气象保障工作,虽然马兰基地已经有了一个负责具体保障工作的气象室,但北京需要一个指挥中心,特别是对原子弹爆炸之后粉尘运动、沉降的方向预判。 当时我们气象室属于作战部,每次有重大任务的时候周总理都会来,我负责向周总理汇报,然后中央再决定是否可以执行。 每次核试验结束之后,日本总会向我们提出抗议,因为粉尘会飘到他们那边。 居住在甘肃的一些老百姓,我们会在核试验之前提前通知他们离开家一段时间,等粉尘过去之后再让他们回来。 从这时候起我就一直负责中长期的军事气象预报工作。”
“后来咱们国家面临全面的核战争威胁,全国的气象台站都要作准备。为了应对核战争,我们在四川搞了一个气象站,对全国的气象进行整编,我当时在那边主要负责技术。 之后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以总参的名义作为气象专家参与了保障工作。 ”
“反正我从事气象工作跑的地方是不少的,做的项目也不少,但是没有多大成绩,就是做了一些工作。 ”
在史老工作的后期,由于总参气象室已经颇具规模,从事中长期气象预测的工作量相对于短期预测较少,史老开始参与一些资料的整编工作、军队备战工作。

61级空军工程系校友 于树藩
校友于树藩的回忆是从进入哈军工之前开始的。
于老说:“我们60级和61级的同学,没有参与高考考试保送入学的。 在入学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学习与军工相关的专业,也从未听说过哈军工。 临近高考,学习很紧张,这时学校通知让我们参加军校的体检。我当时已经近视了,心想就不去参加了,后来我们班主任要求在花名册上的都得去。过了一段时间通知我要政审,我当时还专门去问了一下我体检是否通过了,没想到我戴着250度的眼镜还能通过。 政审结束之后,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团支部正在开会,这时有个同学通知我去学校的书记办公室,进去之后,书记将哈军工的入学通知书交给我,通知我下午去军分区的招待所报道。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负责招生的三系的一位干部,是穿海军服的一名上尉,我们叫他钱队长。 他让我不要回家了,晚上住招待所。我说这哪能行,急哭了,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去哪儿了。后来队长同意我回家告诉父母,但晚上8点前必须归队。 这就是我稀里糊涂进入哈军工的经过。 我的入学通知书是1961年7月14日签发的,我现在还保留着,是一张粉色的纸,上面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招生委员会’的大印。”
“我认为我在哈军工最主要的收获有两点,第一就是身体素质的提高。 小时候我总是咳嗽,我高中的很多同学也都知道我气管不太好,到了军工之后通过入伍训练,每天进行高强度的摸爬滚打,有时,在水泥地或是柏油路上练习匍匐前进,胳膊肘都磨破了。 但三个月训练下来,我整个人确实大变样了,能吃能睡,一下子长了20斤,比喂一头小猪都厉害。 当时总支队长在做总结报告的时候也提了这点,很多同学体重都上升了。 当时虽然是经济困难时期,但是我们没有饿着,军工的领导非常重视学员的伙食。刘居英院长非常仔细的算了学员每天大概需要多少卡路里,每天的配菜都要满足这个标准,那时候我们都不懂这方面的知识,感觉刘院长不愧是北大毕业的,懂得非常多,而且对学员非常好。
第二个收获就是对我人生观的塑造,一方面源于政治课,一方面就是干部的言传身教。哈军工从领导干部到炊事员对学员都非常好。特别是刘居英院长,非常平易近人。我们走在路上碰到他还没来得及敬礼,他就先和我们打招呼了。记得有一次考试结束,因为教室暖气特别好,我们一个个脸都是红扑扑的,路上碰到刘院长他就和我们开玩笑说:怎么样?考糊了吧? 我们当时上街都是要2-3个人一起去,有时候中午会错过午饭,但我们每次回去食堂的后门都是开着的,通过炊事员的工作通道可以走到食堂内,掀开锅盖里面一定是热腾腾的饭菜。 作为学员,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 在校期间我没有任何的思想负担一心就是学习,从那时候我就树立了要永远留在部队,为国防建设奋斗一辈子的人生观。可以说我整个人生最精彩的时光就是在哈军工的五年。”
“毕业之后,我进入空军工程学院任教员,从事为空军培养机务干部的工作。1990年又调至陆航研究所参与陆军航空兵的建设。在2000年我退休之后,中国军事装备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55级空军工程系校友 马金福
校友马金福进入哈军工前,高中就读于上海市继光中学。
马老回忆到:“高考的时候我报了清华、北大,还有南京理工大学,结果录取通知书发下来的时候上面写着军事工程学院。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学校事先都没有和我说。因为八月一号就要去学校报到,我们学校当时算上我还有一个同学被哈军工录取,他是比较了解内部情况的,我是什么也不知道。当时我家子女比较多,生活也比较困难,去军校的话军队能把我的一切吃穿用住全包了,所以我还是决定去哈军工。 报道之后学校又组织我们进行了一次考试,最后将我分配到空军工程系气象预报专业学习。”
1961年毕业之后,马老首先下基层到福建空军连城气象台工作一年,而后回到总参气象局,参与了多次核试验、卫星发射的气象保证工作。
回忆起参加核试验气象保障工作,马老有感而发:“每次实验的前夕我们气象保障部门的人基本上都是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状态,因为在实验状态下我们更新数据的频率是不同的,分为倒计时1周、倒计时3天、倒计时24小时、三个阶段,倒计时1周的情况下,我们每隔一小时就要全面更新一次数据,而进入倒计时24小时阶段,我们需要时时对数据进行分析更新。相比于高度紧绷的神经,条件的艰苦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谈话最后,在校友会一行人要求诸位老校友谈谈过去的成绩、褒奖时,老校友们都哈哈一笑。
于树藩说:“年纪越大,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越是过眼云烟,一个人的成就不能看你有没有几等奖。因为这些奖主要都是有名额限制的,就比如当时我们工资上调2%,但是100个人里面才有2个名额,你要和这么多人去争,所以我干脆就不要了。”
干韫胜补充道:“这些奖励是党为了鼓励大家,既然我们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是革命者,我们即使没有鼓励也照样干。相比于那些倒在解放前的同志们,他们一天福都没享到,更别说什么评职称提干奖励了。”
下午二时许,校友会一行人分别探望了59级校友文裕武(85岁),53级校友崔君望(86岁)。

59级空军工程系校友 文裕武
见到他时,文老拿出了自己成长战斗心路历程的诗集“随録集”,赠送给校友。
其中有他军工毕业时写下的诗词:
军工毕业上总参,一九六四年六月。
六载拼搏如战场, 苦读求知日夜忙。
成绩优秀先分配, 进京工作要自量。
参与谋略责任重, 总部机关新课堂。
他1954年参军,58年考上‘哈军工’毕业后分配到总参装备部,承办航空装备业务,历任参谋、副师、正师职处长、武器装备综合论证研究所所长兼书记。1986年筹建总参陆军航空兵。1992年退休。退休后积极发挥余热,被聘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顾问教授,总参陆航局科技顾问,总装直升机专家组顾问。工作期间,曾立三等功两次,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三等奖数次,一等奖一次,国家科技二等奖一次。

53级校友 崔君望(右一)、61级校友 干韫胜(左一)
崔老是1953年北师大保送哈军工的,54年分到海军工程系雷达专业,58年毕业留系教授会任教。1979年调总参四部54所,历任雷达研究室副主任、主任,90年11月退休。崔君望校友是哈军工北京校友会第一届常务副理事长,专家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他始终深度关注哈军工发展史,发扬哈军工精神,关爱校友们的成长与进步,校友有困难找到校友会,他总会想方设法帮助解困疏难。是一位好校友,好导师。
第三次座谈会
12月23日上午9时许,校友会专家委员会执行委员傅一歌、校友会监事殷红兵带领校友会技术人员翟宇豪、朱永康前往中灿苑开展第三次座谈会,慰问探望老校友。在校友李天升的爱人刘兰青的协助下,本次座谈会的地址选在中灿苑二区六号楼党员活动室。与会者有57级校友王志民(88岁)、61级校友冯善国(79岁)、60级校友边宁(80岁)、58级校友杨松华(85岁)、57级校友李天升(87岁)、刘兰青(李天升爱人)、60级校友叶运均(80岁)、55级校友齐玉简(87岁)、62级校友杨家聪(76岁)、校友联络员干韫胜(79岁)。

前排:校友王志民(左一)、校友冯善国(左二)、校友边宁(左三)、校友杨松华(右三)、校友李天升(右二)、刘兰青(右一)
后排:校友会翟宇豪(左一)、校友会朱永康(左二)、校友叶运均(左三)、校友齐玉简(左四)、校友杨家聪(右四)、联络员干韫胜(右三)、校友会殷红兵(右二)、校友会傅一歌(右一)

58级导弹工程系校友 杨松华
58级导弹工程系校友杨松华首先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为了响应祖国号召,在部队连续两次参加考试终于圆梦哈军工的过程。
杨老说:“当时我们从军队进入哈军工学习的学员,相对来说学习的功底较为薄弱,经过预科之后学习之后我们班只有一半人顺利完成本科的学习阶段。 由于我之前属于自学成才的类型,因此我能顺利完成哈军工这样的学校学习是令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我认为我们哈军工有两大传统是非常值得发扬的。一个是求实,因为我们是搞科技的,要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才能解决问题;另一个是我们的奉献精神,我们国家搞两弹一星,哈军工是功不可没的。当时钱学森在学校提出了系统工程,所以国防科大就以数学教研室和导弹总体教研室为基础组建了系统工程专业(七系)。1989年7月接到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任命书,任命我为该系政委。”
“尽管哈军工1970年被肢解,但是我们作为主体的尖端武器研制的专业却完整的保留南迁。令我特别自豪是我的女儿和女婿毕业于国防科大,算是将家中的哈军工精神传承了下去。”

60级火箭导弹系校友 边宁
导弹系校友边宁为我们第二个讲述。
边老:“我其实从小的兴趣在文艺方面,当时舞校在师大女中招生选了两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父母不同意我去,当时校领导还上门做工作,但我很希望能去从事文艺工作。当时班上还开了两次会,一次是中队开会研究边宁去做什么,结果意见是一半的一半,一半人同意我去舞蹈学校,另一半说现在文艺对国家建设来说不是主要的。没办法后来又开全班的会议,还是一半一半。这时候我父亲的老战友出面做工作,和我讲现在国家急需的是能从事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人才。于是我就进入哈军工继续学习,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是区三好生,直接保送了留苏,但由于60年中苏关系已经破裂,父母和我说去苏联之后高精尖的东西肯定是学不到的,去了也只是镀金而已,建议我老老实实留在国内进入哈军工学习,那是祖国最需要的,我服从国家的需要。”
“在哈军工我因病休学了半年,毕业的时候刚好文革开始,原本已经被分配的我也没走成。当时批判我们是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允许我们去七机部。造反派把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搞得一团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这个时候21基地来要学生,指导员和我说你如果愿意去就赶快去,这样我就来到了21基地,可以实实在在的为国家做事。”
“21基地的条件确实非常艰苦,那时候我们都是住帐篷,早晨起来半个人都睡在沙子里面,食堂也是在帐篷里面,到处都是沙子。当时我们大家主要吃的是高粱饭,每次吃饭前大家都会拿水倒入饭里,上面的饭吃光了再把下面的沙子倒掉,馒头只能用咸盐水泡烂了直接吞下去,完全没有办法咀嚼。这样的状况大概持续了半年,当时要搞导弹和卫星远程的工作,我们就被分到了山东,负责遥测工作。我当时在基地利用业余时间研制了一个误码测试仪,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我们的工作,最后组织上授予了我一个三等功。”
“后来我们的侦察卫星上来了,那时候说实话我们的科技还是走在前列的。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没有用户,测出来的数据谁来把他转化成情报呢?当时首先找了空军,但空军说这个东西我们处理不了,因为当时空军的主要任务是国土防空,还没有走出去。 那我们想既然是有关情报的就找总参吧,总参二部接受了。总参二部主要负责情报工作,过去都是靠人力来搜索,侦察卫星是一种全新的手段,同时也需要新的人才,我就这样被选入总参工作。 我们最早的卫星还是使用胶片来拍摄,后来上海那边有了电子侦查卫星就更加方便。”
“我是搞技术出身,但因为我参与的项目比较多,而且是哈军工出来的,当时军事装备领域的人才基本上都有我们的同学,所以组织上就让我来负责协调各方关系,同时负责卫星的发展建设规划,直到我退休。 后来组织上让我回去,我没同意,因为我一直不喜欢当官只喜欢做事,特别是搞研究。”
“这么多年要说最艰苦的时期就是当年在基地的时候,每当沙暴来临远处的天边就是一条黑线,看着这条黑线越来越粗从我们的头上掠过,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卡车车灯投射的距离只有不到20厘米。我们几个抱着头趴在卡车的车底,用双臂在头前圈出一小块空间可以呼吸,不然根本无法喘气。 但是那时候除了几个上海的当了逃兵,我们都坚持了下来。大家每天都特别高兴,每个人过去之后都是活蹦乱跳的,逢年过节就是天当幕布、地当舞台,又唱又跳表演节目,因为我们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心情特别舒畅。 之后我们的条件就越来越好了,至于加班什么的那都是常事,根本不算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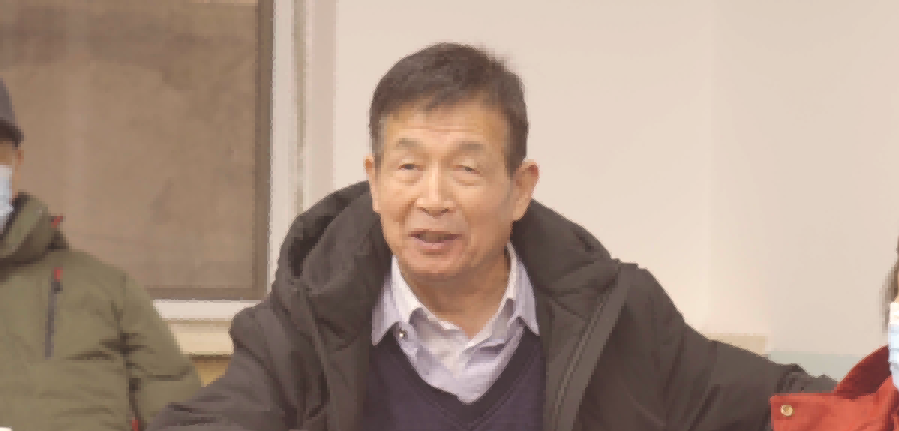
61级工程兵工程系校友 冯善国
工程兵工程系校友冯善国回忆到:“我想说两个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第一个是我认为哈军工的学生们学习都非常刻苦,为什么这样说呢?对我自己来说,我不能说聪明,但是我学习一直非常刻苦。我高中读书的时候,我老家是农村的,距离学校大约有125华里。每次开学的时候,都是挑着担子去上学,前面担着书,后面担着我的被褥,我还是边走边看书,我主要是背俄语单词,一边走还一边拿手指在屁股上比划单词的拼写。我们高中每天晚上9:30熄灯,熄灯之后我就跑到路灯下去看书。 可到了哈军工之后我感觉比较难学的是弹性力学,我当时是弹性力学课代表。记得当时,有一天晚上大概十点钟的样子,我从宿舍出来想找一个有亮光的地方学习一下弹性力学,于是我就去了食堂,打开大门以后我大吃一惊,我本以为只有我自己晚上过来学习,万万没想到每一张饭桌上都坐满了学习的人,当时我很震惊,没想到同学们都这么刻苦。那时候真的令我非常震撼。”
“第二个事情是,1966年我从五系毕业,因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到67年底才被分配。我被分配到52师127团二营八连。当时由于中苏交恶,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大规模的搞人防工事,我这个专业主要就是负责打坑道。记得69年,我们在做天安门电梯井,高度是37米,井筒为钢筋混凝土,浇筑完,垂直偏差只有几毫米。当时我们工程兵的副司令员胡奇才找到我,让我总结一下经验:他们这个电梯井是如何打得这么笔直。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边画图边用文字进行说明,由于要的急,我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完成了任务。我想这就是哈军工精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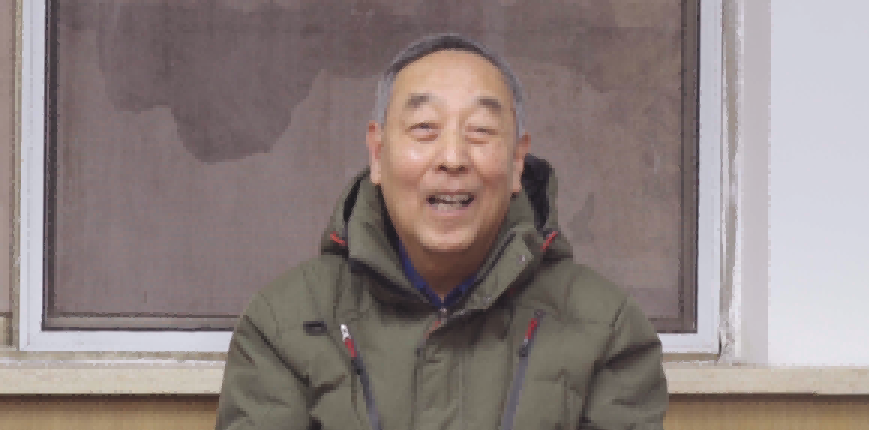
62级空军工程系校友 杨家聪
杨老:“我是空军工程系空空导弹自动控制专业的学生,班号62181。”
“我毕业以后分配到了空军的沧州11航校,经过一年的当兵锻练,我进入了导弹维护中队。半年之后,我又被调到了空军司令部军训部,改行从事航空兵部队的飞行训练工作,这一干就是14年。后来我又被调到了总参军训部、先后在组织计划处和战役训练处工作,最后在军训部退休。”
“回忆我的成长经历,我想谈谈在我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64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当年搞了一次反不良倾向运动。那时候在哈军工要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做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在全班形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我们班当时有三个重点批判对象,第一个是因为瞒着组织谈恋爱,因为这位同学是农村的,谈婚论嫁比较早,但是他来到哈军工以后又没有及时上报,因此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第二个批判对象是因为散布小道消息,说刘居英院长有两个老婆。 我是第三个批判对象,罪名是只专不红。当时全班都对我火力全开,我挺想不开的,我是满腔热情来到哈军工,想为了祖国的两弹一星上天做贡献,结果怎么现在成了批判对象了? 我被大家批判的是痛哭流涕,晚上都睡不着觉。但是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下定决心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我反思自己,因为当时对政治也不是很关心,就埋头搞业务。比如说当时组织‘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反映在基层就是多做好人好事,比如帮别人理发、打扫卫生什么的。 我当时就提出你学雷锋得落实到本职业务上,你得好好学习才能为国家做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学雷锋。 正是由于这些论调导致我遭到了批判,所以我经过反思之后还是决定要爬起来,认真反思做检讨,最后我还做了班长。现在我已是晚年阶段了,再回首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思想向成熟转变的一个过程。在这件事之后无论我遇到什么情况,我都可以做到处变不惊,应付自如,不会因为受到挫折就一蹶不振,也不会因为受到表扬而忘乎所以。”

57级空军工程系/导弹系校友 王志民
王老:“我是1951年抗美援朝入伍的,经军政训练,分到了沈阳的第八航校学习飞机无线电地勤专业。毕业之后我被调到了抗美援朝一线的作战部队----空六师。”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立功入党。1956组织上让我报考哈军工。 我当时连高中都没有毕业,完全不知道哈军工是个什么学校。 经过考试,组织上原本推荐的四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去哈军工上学。 当时学校和我说可以选择是否上预科,我心想我这学习的底子不太行,初中高中都没毕业,我不可能不读预科就去上大学。 但进入预科之后我后悔了,我发现其实我的数理功底还是不错的,应该直接上本科。 入本科时,分配在空军系无线电科,58年哈军工成立导弹系,我被抽调到导弹系地空导弹无线电制导专业。这个专业的课时比较多,本科是五年半制。
从五六年去到哈尔滨,到六三年初才毕业,在哈尔滨呆了八个年头。 当时在哈军工由于我既是军官学员也是党员,所以我担任了党支部书记,负责三个班级的党务工作。 在哈军工的同学们,学习都非常刻苦,晚上教学楼里都是灯火通明,但仍有一些人实在跟不上真的被退学,我们年级就有一个同学被劝退。”
“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当时我还很不开心。 接到通知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午休时间我碰到了我们系主任,我们戴主任笑着对我说:‘你有婆家了。’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国防科委点名要你。’我说:‘不对吧戴主任,我的毕业设计还没搞完怎么就把我分配了?’主任说:‘那我不管,我也管不着这事儿,反正人家点名要你。’”
“我们那时候革命战士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不能不服从分配,但是从我本意来讲,我是希望去搞科研的,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毕业设计是优等,没想到一下给我分到机关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国防科委是做什么的,后来打听才知道,是负责我国国防科研的最高领导机关。但是为什么把我分过去,我也不清楚,也许是看我有在部队的履历。我被分配到了科委四局,主要是负责防空雷达的科研管理工作。七六年总参成立了第四部,主要负责电子战,又把我从科委调到了总参。”
“记得当时打U-2侦察机的时候我们失败过很多次,当时击落U-2侦察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真的是很费劲的事情。 咱们的飞机得做跳高动作上去打,因为飞行高度完全够不着,飞机的性能也不行。 刚开始用导弹还可以,但后来美国人就干扰我们导弹,我也和有关部门到现场调研。抗美援越期间,我们的高炮雷达也时常受到干扰。 于是总参决定,由通信兵部牵头组织通信兵、科委、炮兵组成工作组到战场上去调研。当时的战场环境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美国人经常轰炸,而且百舌鸟反辐射导弹能够直接锁定炸毁我们的雷达车,可是我们雷达不开机就无法捕获他的干扰样式,而如果雷达一开机又会被百舌鸟捕捉,现在想想那段日子还是有些惊心动魄,但当时我们这群人没一个人害怕的。”
“在机关工作主要是负责管理装备科研、搞调研。谈不上有什么贡献,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我年龄比较大,八八年授衔之前我就退休了。退休后,被返聘,主持编写电子对抗工作的发展史,直到七十一岁,才彻底离开了工作岗位。”

55级炮兵工程系校友 齐玉简
齐老:“我1955年高中毕业考入哈军工,上完预科之后,我进入了炮兵工程系大概学了三年左右,我被调到了防化专业,但其实也并没有在这个专业学习,组织上就又把我调到了北大原子能系学习了两年。 在北大学习期间正好赶上了困难时期,我们的学习也并不是特别深入,原本应于1960年毕业的我,恰逢大跃进时期学校要给我们再加一年。但这个时候军队要人,我也就没有继续完成这一年的学业,直接去防化学院当了老师,一直到退休。”
“化学院工作期间我主要是搞科研。 我的第一次任务就是参与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当时我们学院的几个同志一起负责研制遥控的放射性物质测试装置,从设计、测试到投产我们全程参与,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们都呆在工厂里。 当时大家都不了解原子弹的威力有多大,我们的测试站离爆炸中心点大概有7公里,我们在一个地下防御工事里面把线路都提前埋好。 原子弹引爆之后,第一份数据就是我们这个站点上报的,有了这份数据后,总观测站才可以向中央报告原子弹爆炸成功,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当时也立了集体一等功。 回到学院之后我也从事了一些核防护的工作。 我个人觉得在哈军工学习期间打下的基础,给了我之后工作非常大的帮助。”

60级工程兵工程系校友 叶运均
叶老:“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研究数理化,当年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我是第二名,一直就想当一名工程师。我在哈军工学的是地爆专业,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毕业之后是没有选择权的,党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去干什么,我们就是一块砖。”
“适逢我们党开展四清运动,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在毕业之后就被安排去了西安搞运动,我当时因为阑尾炎做手术晚去了一周,并没有赶上发动群众的阶段。到达西安之后我直接就进入了专案组。 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们还查出了一个大日本帝国宪兵队蚌埠分队便衣队队长,而且这个反动分子当时被连续两次连降两级之后还是一名17级干部。像这种反动分子解放的时候都一律枪毙,最后这个汉奸被判了15年。 记得当时反动分子向我打报告要烟抽,我当时由于不会吸烟还专门出去给他买了烟,我也是这个时候学会吸烟的,直到八零年才完全戒烟。”
“四清运动结束之后,我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暂时被分配到的沈阳军区,我到军区报到的第四天,军区就接到了军委开展运动的命令。 由于我刚到不久,师部让到我基层的雷锋部队参与正面教育,当时我们这个班学雷锋运动贯彻的非常好,每次干活回来衣服只要有一点脏,我就得马上洗,不然马上就会有人偷偷帮我洗掉。 ”
“之后文化大革命越搞越大,一直都没有人管我们这批学生,分配的事情也一直搁置,我就在下面的雷锋班一起打坑道。当时打坑道的方式就是抡大锤,我和我战友轮着打50锤,我们每次用力击打,一垂手一下虎口位置就会变得红肿。 在那段时间,因为打坑道有非常多的战友离我而去。 后来我当上了排长,又到了连里的宣传组,始终没有人管理我们这批学生的分配。 我本来是非常喜欢理工科的,没想到这一下就从了文。 后来随着总政文工团的恢复,我又开始编雷锋故事,不久又被调到了解放军文艺社当编辑,专门负责管出书,这一干就是12年。 此外,我当时还负责给首长们写回忆录,接触的开国元勋比较多,随后我去总政办公厅改革编制室工作了三年,被调到了军委办公厅给杨成武当秘书,一直干到退休。”
“我和边大姐(边宁)的境遇截然相反,她是喜欢文艺走了理工科,我是特别喜欢理工科却从了文。”
最后叶老为大家讲述了他参与为数不多的科研项目,有关西德核地雷参数的研究以及如何使用火箭开辟通路,由于涉密,叶老的讲述只能点到为止。

57级空军工程系校友 李天升
李老和夫人刘兰青一起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我是1932年出生的,解放前,我在学校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1947年、1948年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压迫的革命活动。”
“1951年我已在四川自贡曙光中学读高中二年级了,积极响应了国家抗美援朝的号召,参加了志愿军。到成都第四预科纵队学习后,就投入到了抗美援朝战场,在王海大队负责维修飞机。 当年我们这批年轻人对参军都是非常积极的,很多人想进部队都进不了。
我参军之后一直都是搞技术工作,抗美援朝胜利以后我回到部队空军航校担任教员,主要教授机械维修方面的知识。 1957年哈军工从我们空军每个师中招收一名学员,考试的地点是在公主坟旁边的空军大楼,我记得当时刘亚楼等空军将领对我们都抱有很大希望。考入哈军工后经过一年的预科,我进入一系,主修飞机设计。”
“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海军航空兵司令部,之后国防科工委成立,我又被抽调进入了科工委的飞机研究院603所。主要负责大型飞机的研制工作,包括战斗机、歼击机、轰炸机、水上飞机(歼-7、歼-8、运-7、运-8等)”
“当时我们国家飞机设计的条件有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大型的风洞,小型的风洞吹出来的数据都不是特别精确,在吹风阶段,我基本在绵阳。 到了数据计算的阶段我们又转战到汉口,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最大的计算中心在汉口,我记得当时有一次我的夫人来看我,那次实验计算打出的纸条堆了好几摞,那会的计算机性能也不如现在,计算一次数据至少需要一个月。”
“说到这个计算的问题,当时组织上给我们哈军工的学生,人手发了一把计算尺,而同期的清华、北大每个班才有一把计算尺。 无论什么样的新装备进到国内,总有一套会分给哈军工做研究。所以想想看,哈军工真可以说是国家用金子堆起来的学校。”

李天升与夫人刘兰青
李老的夫人刘兰青补充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阶段他的工作非常辛苦,当时他是课题组的负责人,不仅要带领大家攻坚克难,还要负责百十来号人的其他事情。 那会儿不是说他总不回家,而是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家的概念了,心里都是国家,没有自己的小家。 设计工作完成后还要参与试飞,每天从北京飞广州,早晨吃过早饭就着急忙慌地前往飞机场,所以到现在他吃饭还是狼吞虎咽的。 其实他可以不参加试飞,但是因为他是负责人,他不去谁去,只有他去。早晨在家吃完早饭,午饭就在广州解决,晚上再赶回来,试验飞机各个方面的性能。”
“文革期间,他没有参与政治运动,实验室的钥匙都是由他保管,每天就是潜心搞研究,他还利用这十年时间自学了英语,达到了能独立看小说的水平。他曾经用英语在第六届国际创伤研讨会上宣讲了自己的论文。 在这方面我要向他学习,我俩既是夫妻,也是战友。文革结束之后,要恢复军事院校,78年他又到了总参,参与导弹的研制,被选调到总参的工程技术学院完成教学及科研任务。”
“我这次利用几个晚上整理他的材料,才知道他参与了我们国家十几个飞机机型的设计工作,研究成果弥补了16项国家空白。尽管这一辈子他也没得到什么荣誉,但他总和我讲,他能从一个贫农的儿子走到今天,非常知足。他的行为感动了我,所以我想让大家能知道他的事情。”